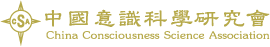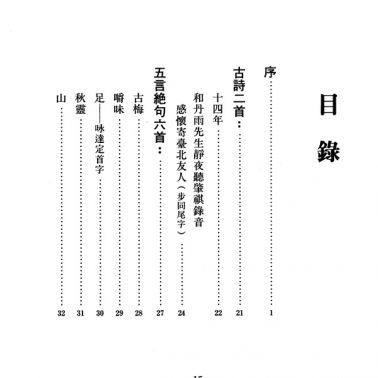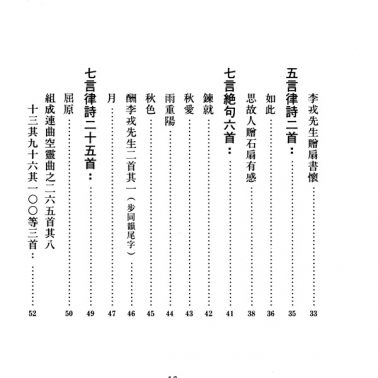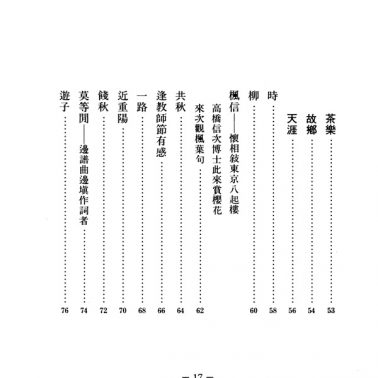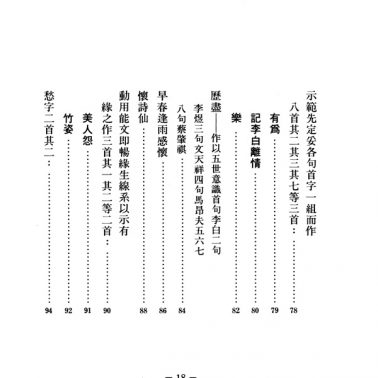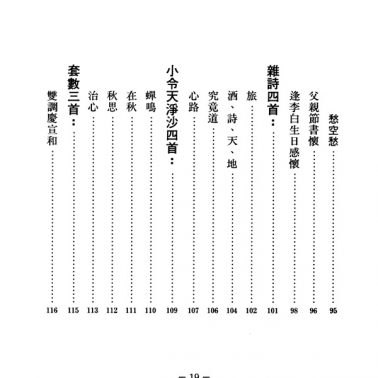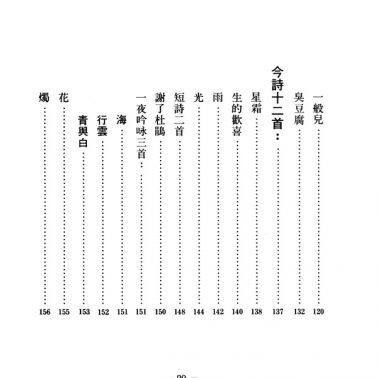飄逸空靈

(蔡肇祺詩選)
- 作者:蔡肇祺
- 發行所:中國意識科學研究會
- 出版日期:1990/10/5
購書資訊:
- 光華雜誌社網路書店
- 若採用郵政劃撥方式購書,請連絡光華雜誌社有限公司,洽詢運費和劃撥手續費。(02) 2507-2807
序
作了四十多年的詩了。只對詩的一股熱愛,時而會促使我拿起筆和稿紙,寫下了當時點浮在心頭的感觸、感慨,而就這麼地寫作了很多詩。
我的詩,槪括了古詩、今詩以及雜詩、詞、散曲等,想作甚麼就作了甚麼;若說迄今沒作過的,那就只有辭了。其中,爲了救人心魂,七言律詩也就作得特別多,因要把它組成爲七言律詩連曲的緣故。這裏我所說的古詩,則已包括了絕句與律詩。
無論怎麼說,詩的用字,總是比文少。因此,作詩的最基本功力,就是無一句離題。而用字簡單、用句通俗,乃成好詩的必需條件;這由李白的「靜夜思」,即可明白。
作詩的功力,絕不可表現成用字艱澀。其實,古來,會作詩之人,其用字都很簡單,而其用句也都很通俗。作詩的功力,乃愈深,則愈能使用簡單的字與通俗之句,來表現成高度文學水準、水平之作。
使用典故,乃是作詩的一種措施,尤其是作古詩。然而,使用了典故,則一首詩如成自五十六個字的七言律詩,其典故而外,純屬作者自己所表現出的字數,便也就較少,即純屬作者本身的創作的内容與表現之力,便須打折扣。所以,我的詩,除了年輕時候的作品外,幾乎都不刻意地使用典故,或都不用典故。這,除了上述的理由而外,爲了合時,能直接地表現出,讀者便也較容易明白。但,有的,我就把典故化成爲自然流露或無形,這樣,行家與一般讀者,便都能受用:懂典故之人,可知典故的另一表現法;不懂典故之人,能依其所知而單純地明白含意。作詩的功力,並非使用典故爲高,那是一種錯覺,因爲,當今的時勢,已異於唐朝。
詩,斷然與文相異,尤其是今詩。今詩,絕非把白話文分行寫成的東西,那還是文,而非詩。因爲,詩句,絕非文句。雖然,一篇好散文,讀起來會具如詩的韻律,然而,那還是一篇散文,而不是一首詩。這,如何分別?只有多看、多作一途!
唐朝的時候,地球上,除了中國而外,也有外國。而今人所說的古詩,在那時候,絕大部分,也是當時的今詩,可是,先人却沒採用外國語文詞句於其詩之中。這是事實!其實,每一個古老的國家,都有其道統存在,所以,生爲一個泱泱大國的中國人,當然不必落魄到採用外國語文詞句於其所作詩中!此乃我的淺見。
散曲中的套數,現在作的人很少,我也作得並不多。而我作的,到踏入心國不久,還依其牌格來作,但,其後,明白了自己曾活過了馬昂夫一世,於是,爲了使元朝散曲的特色,能表現得淋漓盡致,尚且,亦使今人能不至於礙於難記住牌格而就却步於習作它,我也就不依牌格地作起了它。然而,倘曾活過元朝,而又成名於作散曲的那一世意識,沒流露到今世的表面意識,則今人而要作散曲的套數,乃是一件極不容易之事。至於散曲中的小令,我通常作的,則以天淨沙爲主。
詞,起自李白,而李煜打牢了底子,以至大盛於宋朝;而我,也活過了李白與李煜二世。而因李煜,於當時,就已把其後人稱做「詞」的作品,都稱做「長短調」地但强調其用句的長短爲該類作品的特色,所以,踏入心國之後,我就不按詞其牌格地作起了詞,且把它歸類於「雜詩」之中。至於樂府,則我也把它歸類於雜詩之中了。
唐朝之前的先人,留下了辭、古詩、樂府;唐朝的先人,留下了以今人來說也屬古詩的五、七言絕句、律詩;唐宋先人,留下了詞;元朝的先人,留下了散曲。而今人,要留給後人的,在詩的範疇裏,當是甚麼?應該就是今詩罷?是「今詩」而非「新」詩,因爲,唯有「今」,纔對得起「古」;「新」,則只能對「舊」而已。我,只聽說過把個人其先前作品稱做「舊作」,却沒聽說過把唐朝以前的先人的詩作,稱做「舊詩」!難道中國人,眞的非落魄到連詩類也定要學外國人的稱呼不可?今人眞的以爲中國的道統無一可取了?「古」,明明是對「今」啊!我覺得:今人,必須把先人留下來的好東西發揚光大,且又必須留下代表我們這個時代的好東西給後人。因此,作詩,不可只偏於先人留下的類格,更不可不理不睬先人留下的類格,而只一味地作自以爲的或如外國人作的今詩。那都乖離中道即中庸之道。而其結果,又必會產生不同愛好之人的互相排斥,以至遺害文化。宋朝的詞,等是其時的今詩,可是,蘇軾却不僅詞好,古詩也很好,只憑其七言絕句「花影」,不就堪稱千古絕唱?人而有緣並世而同好以詩,則應該攜手發揚自己的國家屬於詩範疇的文化,不該互相輕蔑、排斥,那只不利於個人、國家而已,應是君子不爲!這,也是我的淺見。
我作的七言律詩,可分爲三類:一是供組成連曲的;一是爲例治心十三法的;一是不供組成連曲,非爲例治心十三法,我稱它做單首的一般性的。供組成連曲與爲例治心十三法的,乃以救人心魂爲主,並不全屬純文學性,前者,雖也集了三首,但在這裏,我却不想談及,有興趣,則請參閱拙著「七言律詩五一五首」。而在這裏,則僅提我稱它做單首的一般七言律詩。這種七言律詩,除唐朝爾來已成爲規格之項目外,我又自加了三項規格,這樣,能方便於今人作成好七言律詩。這三項規格如下:
(一)必須大工對。所謂大工對,就是三、四句的用字,倘於五、六句又用到,則五、六句其字所對的用字,須與三、四句其字所對的用字相同。
(二)一首八句,其並排横列用字,不可相同。
(三)一首八句,其二、四、六字的平仄,可不合乎古來規格者,以十字爲限。但,這個時候,若以一般格論,已超過了十字,則可論以王維格或李白格、杜甫格或通明界格等,如此,則或未超過十字。有關這數格之内容,則請參閱拙著「七言律詩五一五首」第五章中的「通用七言律詩規格」。
我,十三歲起愛詩、作詩,現在已五十七歲。說漫長也是漫長的這四十四載歲月,其實,却會在短暫的一趟人生裏,輕易地流了去!十多年來,我,詩,作得很多,可是,留下來的,却不到其十分之一。這,或許是當場作給呌我老師的有緣參考之作,佔了很多所致。因爲,面對着呌我老師的有緣,我很清楚:我該做的,僅是使對方眞的能詩、會詩,而絕對不能爲了顯露自己的才華、功力!就是由於堅守這個原則,我,一個晚上雖作了二、三十首,但,堪做爲夠格稱該時點的拙作者,便也寥寥無幾了。而在這種場合裏,我作詩的速度,乃只費在疾寫的時間而已者爲多,不管其詩的種類、題、韻等,是自定,或對方指定,或全照對方的。
詩,必須以眞、善、美中的眞爲主。這也就是說:詩,必須以合乎實際爲其骨幹,而其實際,又必須實際在其人的身的經驗、心的經驗、魂的經驗。而在不能兼顧眞、善、美三者的狀況中,作詩必須先把握到的,是眞,而非善或美。當然,最好是眞、善、美三者都能把握到,不然,就只把握眞與善兩者,或僅僅把握住眞。這,也是我作詩的一個原則。試想:人而妄言,則已屬非,那麼,人所作的詩,又怎麼可以存有妄詞、妄句?不實際、不眞,豈非就是妄詞、妄句?其罪,又豈止於不知愁而强說愁而已?
浮了思,就疾速地寫出整句,最好是一整句接着一整句到成首。這是作詩的要領。不要想了半天,也寫不出一句;不要想了一會兒,纔寫出半句;不要即使不想就能寫出,但只是半句;不要一會兒就能寫出一整句、數整句了,却無法再接下一整句又一整句到成首。那即使終能作成了一首詩,却要屬好詩,則很難!合乎作詩的要領而作成了首,倘覺得有所不妥,就修改它成完整,於其即後或其翌日,一次,再一次地。這是成詩的途徑。
作詩,不要怕别人看般偷偷摸摸地作;這樣,即使作得出好詩,却也上不了大雅之堂。因爲,有人曉得你會作詩了,則有朝一日,便很可能會有同好者,來和你酬和詩。而等對方一寫詩給你了,你能不酬和他嗎?這是中國的道統呀!何況能詩、會詩之樂,且盡在酬和之中!僅可獨自一個人在般地作慣了詩,則一逢到有別人在的場合,就會作不出詩來,這樣,則怎麼能在酒逢知己千杯少的場合中,來和人家論詩而酬和呢?所以,我纔敎有緣,於多人在一起的當場,作得出詩,作得成詩,且要在短時間内。詩的酬和,大都以古詩爲主,而我也但具酬和古詩的經驗罷了。其所以會是古詩爲主,乃因古詩,具固定詩格之緣故。倘無規格可循如今詩,則又怎麼去步同韻或同韻尾字、同尾字等地酬和呢?但,這,並不就斷定了詞、散曲、今詩等的無法酬和;倘雙方的關係是知己、知音,則相信那還是有其可能的。這裏,我只是在鼓勵讀者,養成於和别人在一起的場合,也作得成詩,這麼地過來,纔容易享到酬和之樂罷了,只因酬和詩,乃是愛好詩之人其一大享受。
詩,原本就是人的至情表露出來的東西。由於發自至情,所以纔袒露純潔、樸實,於是,就含有了眞;由於發自至情,所以纔彌漫慈愛、正氣,於是,就含有了善;由於發自至情,所以纔撩起共鳴、嚮往,於是,就含有了美。而詩所含有的這眞、善、美,也就自然而然地與天籟好合了韻律,使詩一被眞的能曲、會曲之人譜上了曲,就淋漓盡致地表現出其内容來。這也就是我所以時常會感慨:「要作成好歌,則必須先有當其歌詞的好詩。」,其原因。然而,這,並不是說好詩就必能作成好歌;其實,詩,有的,却是無法作成歌的。只是能作成歌之詩,倘其爲好詩,則作成了堪定案之歌,就必定是好歌罷了。而我所說的「天籟」,即是動用通明界即天上界的天日界以上諸次元世界之光或全容界諸區直接現象化之光,來作曲所成之歌。
集在這裏的六十四首詩,是我四十四年來所作之詩的精華。爲了使容易數稱,詞與散曲的數做「闋」,我也都數爲「首」了。這樣,較方便於綜合其數稱。
由詩,可知其人。這句話,對我來說,很正確。面對這六十四首,我,如同看到了光陰流水中的我的影子。詩,亦可看到其人的足跡。這,對我來說,也很正確。這六十四首,確確實實是我今生迄今的足跡。我這影子、這足跡,倘能有用於有緣之人的爲人以及走正其人生些許,則萬幸!
公元一九九○年
八月十五日十三時五十三分